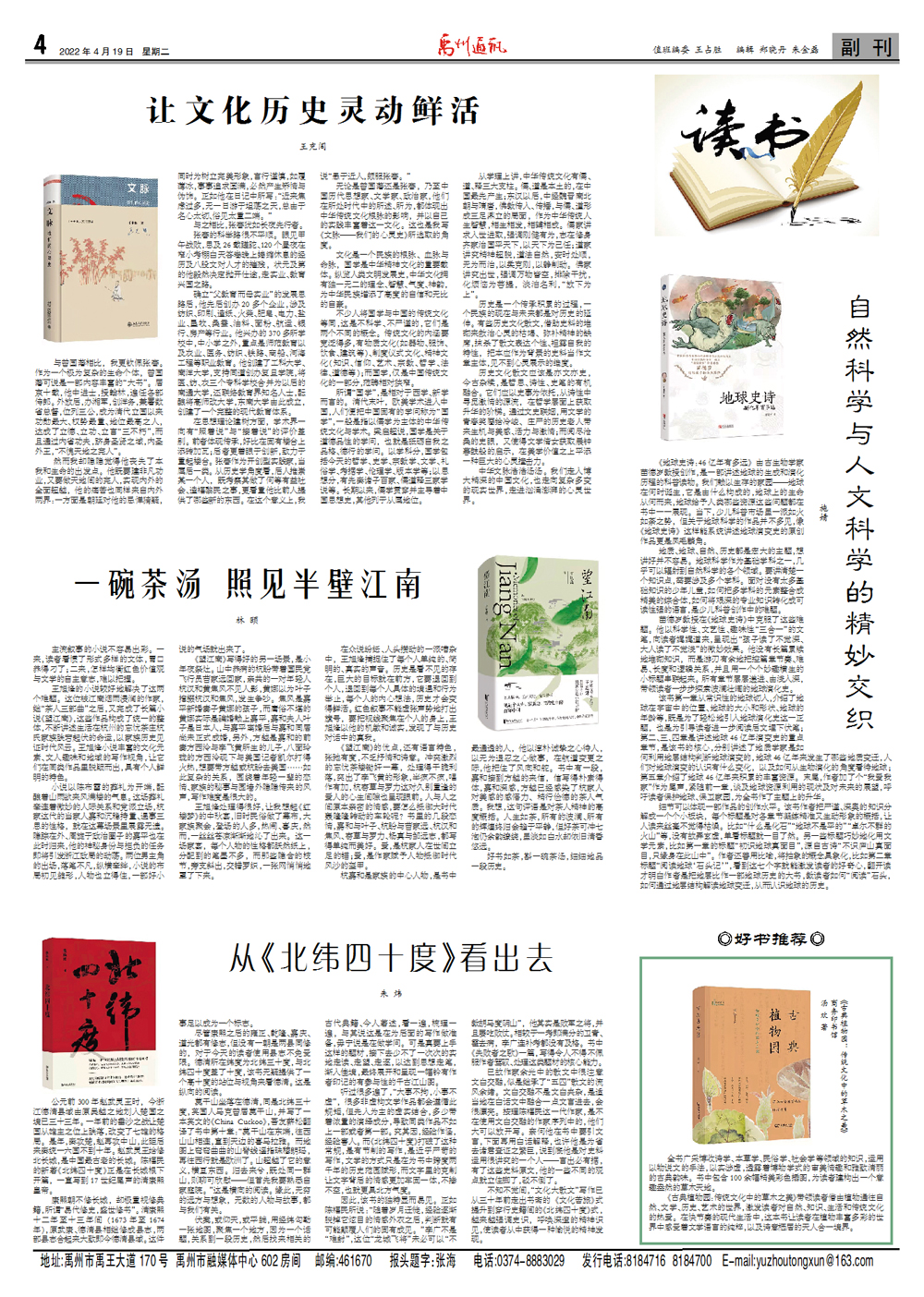
从《北纬四十度》看出去

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时,今浙江德清县域由原吴越之地划入楚国之境已三十三年。一年前的垂沙之战让楚国从雄主之位上跌落,改变了七雄的格局。是年,秦攻楚,赵再攻中山,此距后来秦统一六国不到十年。赵武灵王始修北长城,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陈福民的新著《北纬四十度》正是在长城根下开篇,一直写到17世纪尾声的清康熙皇帝。
康熙朝不修长城,却极重视修典籍,所谓“易代修史,盛世修书”。清康熙十二年至十三年间(1673年至1674年),原武康、德清县相继修成县志,两部县志合起来大致即今德清县域。这件事足以成为一个标志。
尽管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都有修志,但没有一朝是两县同修的,对于今天的读者使用县志不免受限。德清所在纬度为北纬三十度,与北纬四十度差了十度,该书无疑提供了一个高十度的站位与视角来看德清。这是纵向的阅读。
莫干山坐落在德清,同是北纬三十度,英国人马克曾居莫干山,并写了一本英文的《China Cuckoo》,吾友薪松翻译了书中第十章:“莫干山在东端,往西山山相连,直到天边的喜马拉雅。而地图上弯弯曲曲的山脊线遥指珠穆朗玛,再往西行就是欧洲了。山超越了它的意义,横亘东西。归去来兮,既处同一群山,则聊可欣慰——但首先我要熟悉自家庭院。”这是横向的阅读。缘此,无穷的远方与想象,无数的人物与故事,都与我们有关。
伏案,或仰天,或平躺,用经纬勾勒一张地图,聚焦一个地方,因为一个话题,关系到一段历史,然后找来相关的古代典籍、今人著述,看一遍,梳理一遍,与其说这是在为后面的写作做准备,毋宁说是在做学问。可是真要上手这样的题材,接下去少不了一次次的实地走读、走望、走逐,以达到思想走笔,渐入佳境,最终展开和呈现一幅钤有作者印记的有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
听过很多遍了,“大事不拘,小事不虚”,很多非虚构文学作品都会遵循此规矩,但先入为主的虚实结合,多少带着浓重的演绎成分,导致同类作品不如上一部或者第一部。究其因,经验作怪,经验害人。而《北纬四十度》打破了这种常规,是有节制的写作,是近乎严苛的写作,文学的方式只是在为书中跨度两千年的历史范围赋形,而文字里的克制让文字背后的情感更加牢固一体,不掺不空,也就更具北方气度。
因此,该书的独特显而易见。正如陈福民所说:“随着岁月迁徙,经验逐渐脱掉它炫目的情感外衣之后,判断就有可能颠覆人们的固有成见。”李广不是“难封”,这位“龙城飞将”未必可以“不教胡马度阴山”,他其实是败军之将,并且屡吃败仗。相较于一考即满分的卫青、霍去病,李广连补考都没有及格。书中《失败者之歌》一篇,写得令人不得不佩服作者驾驭、处理这类题材的核心能力。
已故作家余光中的散文中很注意文白交融,似是继承了“五四”散文的流风余绪。文白交融不是文白夹杂,是适当地在白话文中融合一点文言进去,会很漂亮。按理陈福民这一代作家,是不在使用文白交融的作家序列中的,他们大可以放开写。奈何他在书中要引文言,下面再用白话解释,也许他是为省去诸君查证之繁巨,说到底他是对史料运用很讲究的一个人——言出必有据,有了这些史料原文,他的一些不同的观点就立住脚了,驳不倒了。
不知不觉间,“文化大散文”写作已从三十年前走出书斋的《文化苦旅》式提升到穿行史籍间的《北纬四十度》式,越来越强调史识,呼唤深邃的精神识见,使读者从中获得一种愉悦的精神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