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植物敞开生命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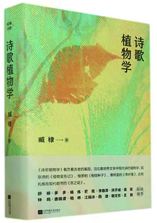
在臧棣新近出版的诗集《诗歌植物学》中,我们迎面与各种植物相遇。这些诗歌植物参差错落、葳蕤繁茂,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自身和植物的关系,“醒目如我们从不知道,我们从前有一个绰号叫盲人”。
在现代的城市景观中,植物和生命的关系已经变得若即若离。植物蜕化为街边的行道树、公园中修建得整齐的观赏花草,或者偶然在转角处挣扎生长的杂草,它们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存在,点缀在审美和生活的边缘。它们不再像诗经时代的植物一样,是我们爱情、劳作和征战的起兴与见证,紧紧嵌入我们的生活。而臧棣的这部作品,再次激活了植物对生命的意义。植物作为生命的存在境域,再次在诗歌中得以澄明和彰显。从对象化的植物前退身而出,重返生命与植物互渗互喻的现场,《诗歌植物学》提供了一片繁茂的热带雨林,让读者置身其中。
《诗歌植物学》共三卷,291首诗,可以看作向“诗三百”略显谦恭地致敬。其中卷一127首诗歌,主要写花草类植物;卷二89首诗歌,主要写木本类植物;卷三75首,主要写可食用的植物。臧棣对于自然主题、自然意象的书写极为偏爱,但是,当植物上升到“学”时,我们就不能够再将《诗歌植物学》中的植物仅仅看作“自然意象”。这部诗集不仅是多首书写植物的“咏物诗”合集,而且是以一种整全与系统的想象力对生命中的植物进行的诗歌观照与秩序整合,这些诗歌植物最终建构了一种完整的生命生态。
作为诗歌的植物学,臧棣在诗集中展现了细节的发现力。诗歌植物学无法用科学的语言去定位植物的科属特征,而是用想象力去发现甚至发明植物新鲜的细节美。这种细节在臧棣的诗中比比皆是。比如《青蒿简史》中,“在这些菊科植物身上,绝对的清香,从来就没被地方性迷惑过”。像这样的细节发现与发明弥漫在诗集中,成为诗歌植物学的氤氲底色。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种细节的想象力发现,更多指向一种生命和植物的生成性关系——此时此刻,植物向生命闪现它之所是!这是一种即时的观看,也包含着一种臧棣称之为灵视的“看”,一种集洞见、见识、直觉、异想、视野于一体的观看。正是观看,才能从惯性的生存中开辟出另一个鲜活的植物学世界。
作为生命的生态学,臧棣在诗集中展现了一种涵括万有的包容力。从高贵的红梨到卑微的狗尾巴草,从挺拔的乌榄树到萧萧的枯枝败叶,从生与死的纠结中提炼出樱花的美到魔术表演生命尾声的柠檬,从“时间像一口绿色的钟”的脆弱黄瓜到“腰身纤细,绿得令翡翠都有点嫉妒”的韭菜,臧棣展现了所遇皆诗的创作活力与包容力,甚至仅仅在《文化人类学考试入门》一首诗中,臧棣就涵括了35种植物,展示了诗人处理植物素材的笔力。所遇皆诗,绝不仅是勤奋能够解释的,而且展示出诗人涵括万有的胃口与语言更新的能力。就像臧棣所说,在素材的意义上,诗无所不在。诗可以在任何事物中找出并还原它自己。在诗集中,诗人则在所见所遇的植物中找到并还原了植物自身。所有的植物,在词语中,回归到属于自身的位置。正是这种植物的各得其所,才使生命的生态学成为可能。只有细节的发现力构不成洋洋的诗歌植物学大观,还必须有这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涵括力与整合力,这样才能在诗歌中容纳下一片繁茂的、热带雨林般丰沛的植物学园林。也只有在这样的诗歌植物学的世界中,我们才可能“更深刻更持久地为大自然迷人的真相所感动”。
《诗歌植物学》展现的是植物、词语与生命的互渗与互喻,其中,词语,或者说语言的技艺,不仅是联通植物与生命感觉的通道,而且是植物与生命互渗互喻的鲜活战场。或者说,只有在词语展示的场域中,植物与生命的互渗互喻才是可能的。由此,诗歌的植物学翻转为植物的诗歌学,对《诗歌植物学》的阅读则从“多识于花鸟草虫之名”的古典阅读翻转为“剥洋葱剥到的空无,恰恰是对我们的一次解放”的阅读解放术。在作品中,词语与植物互渗互喻成为符号他者,并锐利地楔入词语与生命互渗后的抒情主体。词语与植物、词语与生命、植物与生命的相互渗透不是为了凝固成一种生命感觉,而是向读者发出邀请。
对《诗歌植物学》的阅读不是为了重新将臧棣的那些新鲜的比喻进行印证与重复,而是获得一种指引:在与植物相遇的瞬间,植物、词语为生命敞开了一个生动的出口,在那里,我们将重建属于自己的植物世界与生命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