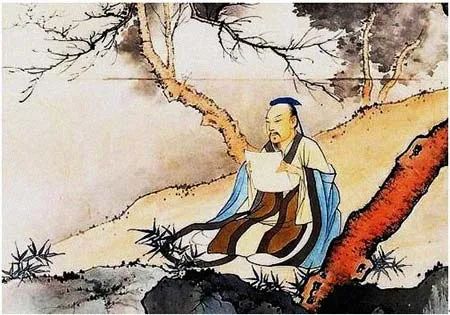胸襟旷达的枢相张昇
张昇(991-1077年),字杲卿,宋代阳翟人。但《宋史·张昇传》却记为“韩城人”,甚至禹州旧志也没收入张昇的传略。那么,为什么又说他是阳翟人呢?这要从一个故事说起。
曾与寇准同为宰相的毕士安有个曾孙叫毕仲衍,字夷仲。祖荫为阳翟主薄。经当地军事长官方镇允许,报朝廷批准,由县人张昇牵头办乡学。办学经费根据设计计算发动民众捐助。
当地有个叫马宏的痞子,在大街小巷搬弄口舌,说什么:“这次张公办学,县令将乘机向百姓们搜刮钱财,由十、百、上千,乃至千万也不止,将使豪绅们不堪重负啊!如果大家给我百两银子,我就能免除你们的这项赋役。”众豪绅们相信了他,给了他百两银子。他却跑到县府宣称:“县官们已经全部私吞了办学经费,又将继续摊派了。”听到这种传言,张昇就起了疑心。他请求暂时停止办学,并将传言公布于道旁。县令准备上疏申辩。
主薄毕仲衍说:“没啥益处,不如抓住马宏整治整治,不用申辩理就直了。”于是,县官们研究决定抓捕马宏,五天后他终于承认是自己捣鬼,并把真相对张昇说了,他被流放到了邓州,全县人相贺。住在那里的给事中张问对毕仲衍说:“谚语云‘锄一恶,长十善’,你这就是啊!”
这个故事记在《宋史·毕仲衍》上,说明张昇本来就是阳翟人。那么,怎么会把张昇记作韩城人呢?
原来,历史上阳翟人习惯将阳翟称之为韩城。战国时期阳翟为韩都,留下了诸如韩王宫、大韩城、小韩城等许多遗迹。文人们写东西往往以《韩城记事》、《韩城集》等为书名。而张昇正是有一本《韩城文集》,才被编《宋史》者记为“韩城人”的。真是“差之两字,谬之千里。”这说明张昇不仅是阳翟人,而且在他做官之前就已是一位热心办学的士绅了。
祥符八年(1016年),张昇进士及第,初仕楚丘(今河南滑县东)主薄。南京留守王曾称赞他有三公辅相之器,夏竦任陕西经略使时也举荐他有才华。他的仕途比较顺利,先后任过掌管财赋的度支员外郎,掌诸王居址的六宅官,掌泾原、秦、凤三州兵马屯戌,训练、器甲、差役的都监等。他以母亲年迈想请求离家近一些,以后当过山西绛州知州、京西转运使、邓州知州、户部判官、开封推官、知杂御史等。
这时,靠侄女张贵妃得宠的张尧佐突然官运亨通,当上了开封知州,张贵妃的亲信内侍杨怀敏也被弄进宫中,引起了公议。张昇性格质朴,说话不择言词,斥责张贵妃不过是一妇人,她的亲信杨怀敏得势,将不比刘季述好到哪儿去。宋仁宗看到奏章后很不高兴,问谏官陈升之。陈升之说:“这都是忠直之言,不刺激陛下,陛下会改正吗?”仁宗方释然,提拔张昇天章阁侍制执掌庆州(今甘肃庆阳县),改龙图阁直学士执掌秦州(今甘肃天水南或陕西南郑县)。
当地的少数民族青唐番部蔺毡部落,原来一直居住在古渭水一带,与夏人有积怨,因为害怕而把地献出去。代理元帅范祥没考虑那么长远,决定在那里建城,那些人怕逼得太紧举兵反叛了。张昇到任后,请示不要建城,而皇上让户部副使傅求审定,认为城不能舍弃,这就形成了战争。先由副总管刘焕讨伐叛将不能取胜,张昇命其他部将郭恩代替,叛将却被打败了。刘焕不仅不给郭恩记功,反告郭恩滥杀老幼,目的是撼动张昇。朝廷命张方平守秦州,调刘焕去泾原,调张昇去青州,准备治张昇的罪。张方平请辞说:“刘焕和张昇的级别就不一样,今天各打五十板,副帅有错让主帅同坐是不对的。”于是,张昇就又留任了。
至和二年(1055年),张昇被召兼侍读,拜为御史中丞。宰相刘沆因御史范师道、赵汴曾揭露过他的过错,想报复他俩将其挤出朝廷。张昇即上表为二御史打抱不平。结果皇上反罢了刘沆的宰相,赞扬张昇能切中时弊,敢于仗义执言不怕孤立。张昇说:“我仰托圣主的福当上了侍从,是不孤立的。今天拿着俸禄滋养奢望的臣子多,而赤胆忠心想着国家的少,我真感到皇上孤单啊!”仁宗很感动。
原来的契丹主宗真派使者带着他的画像来,也想得到仁宗的一张画像。仁宗的像还没画成,宗真却死了。他的儿子洪基即位,发出邀请,皇上让张昇出使,并希望交换新主的画像。契丹却提出先让仁宗的像送去他们才给。张昇说:“过去他们是当弟弟的先送给哥哥画像,现在的契丹主洪基成宋主仁宗的侄子了,咋能让他伯伯先送像呢?”到底还是契丹新主的画像送来后才给他。皇佑三年(1051年),张昇被提拔为枢密副使,又二年参知政事,又一年为枢密使,被称为“枢相”。
当了宰相的张昇仍很节俭,凡上面发一些东西给他,他往往推辞不要。见到仁宗年纪渐老,数次上书劝立太子,终于与韩琦共同拥立赵曙为太子,他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英宗即位以后,拥立新王立了大功的宰相张昇却屡屡以老辞官。英宗说:“太尉为皇室如此操劳,以后每五天到枢密院看看,进宫见朕不必行大礼。”司马光上书说:“近年来,老大臣很多人不安心,一些好说事的人会攻击他们保名夺利。其实,不想进取的年轻少壮也白搭,想干事的老也无妨。像张昇那样清直之人,在位上决不会误事。”但张昇一直请辞,才于治平二年(1065年)七月准罢相养病,四年正月又请他任彰信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许州,后改镇河阳三城节度使,闰三月以太子太师致仕。
谁能想到,人仕五十一年、当了十六年宰相的张昇,退休后竟然“生计不丰”。他回到家乡阳翟,在嵩阳紫虚谷(位于禹州西部,详址无考)搭了个草庵,以“荻簾纸张、布被革履”生息。每天早晚焚香读书,悠然自适,还写了一首《满江红》励志曰:无利无名,无荣无辱,无烦无恼。夜灯前、独歌独酌,独吟独笑。况值群山初雪满,又兼明月交光好。便假饶百岁拟如何,从他老。知富贵,谁能保。知功业,何时了。算箪飘金玉,所争多少。一瞬光阴何足道,但思行乐常不早。待春来携酒殇东风,眠芳草。
张昇于熙宁十年(1077年)农历十月去世,时年86岁,被追赠司徒兼侍中,谥曰康节。